【www.myl5520.com--书摘名言】
11-渊骞
篇一:荀子三十八篇
法言義疏十六
淵騫卷第十一〔疏〕吳曹侍讀元忠云:「漢書藝文志:『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本注云:『法言十三。』此十三篇,即本傳之十三卷。文選班孟堅答賓戲注引作『十二卷』者,宋祁校本云:『李軌注法言本,淵騫與重黎共序。』知軌據漢世傳本,重黎、淵騫并為一篇,故合法言序為十三篇,可由祁校語得之。」榮按:李本自學行卷第一,至孝至卷第十三,每卷標題下皆有注語,惟淵騫卷第十一下無文,蓋重黎、淵騫本為一篇,多論春秋以後國君、將相、卿士、名臣之事,以其文獨繁,倍於他篇,故自篇中「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以下,析為卷第十一。雖自為一篇,然實即重黎之下半,既非別有作意,遂不為之序。弘範知其然,故於此卷標題下亦不為之注。藝文志「法言十三」,此據卷數言之則然,若論其作意,不數淵騫,則止十二。答賓戲注引揚雄傳:「譔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此可證舊本漢書此傳承用子雲自序,其文如此。卷末所載法言序中之不得別有淵騫序,更不辯自明。淺人習見通行法言卷數皆為十三,疑雄傳「十二卷」字為「十三」之誤,又疑淵騫獨無序為傳寫闕失,遂改「二」為「三」。且妄造「仲尼之後,迄於漢道」云云二十八字,為淵騫序,竄入傳中。於是雄傳此文不獨非子雲之真,亦並非孟堅之舊矣。君直據選注此條,證明重黎、淵騫共序之義,至為精覈。然謂軌據漢世傳本合法言序為十三篇,似亦未協。李本法言序附孝至之後,明不以為一篇。蓋重黎、淵騫之析為二篇,漢世已然。謂法言序無淵騫序,則是;謂十三卷為數序,不數淵騫,則非也。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如其寢!」〔疏〕「淵、騫之徒惡乎在」者,學行注云:「徒猶弟子也。」淵、騫之徒,猶云七十子之弟子。仲尼弟子列傳以顏淵、閔子騫居首,故舉淵、騫以統其餘也。音義:「惡乎,音烏。」按:七十子皆身通六藝,而其弟子多不傳,故以為問。「寢」者,廣雅釋詁:「寢,藏也。」按:謂湮沒不彰也。音義:「曰寢,俗本作『曰在寢』,『在』,衍字。」司馬云:「宋、吳本作『在寢』。」按:此因未解寢字之義而妄增者。「攀龍鱗,附鳳翼」者,伯夷列傳云:「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云:「喻因孔子而名彰。」即此文所本。巽以揚之,集注本無「巽」字,云:「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從李本。」是溫公所見監本無此字。今治平本有之,而「巽以揚之」四字占三格,明是修板擠入。秦校云:「當衍『巽』字,溫公集注可證。」是也。俞云:「盧氏文弨云:『李本巽作翼。』不知翼者即涉上句『附鳳翼』而誤衍。溫公但云『揚,發揚也』,不及翼字之義。是其所據本無『巽』字,亦非別有他字也。今各本皆作『巽以揚之』,蓋據宋、吳本加,非李本之舊。」榮按:舊監本固無「巽」字,然此或傳寫偶脫,非必李本如此。後漢書光武帝紀章懷太子注引此文正作「巽以揚之」,(各本皆同。)則其所據本有「巽」字,為宋、吳本所自出,錢本亦有之,於義為足。蓋下文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即承巽字而言。巽為風,故云勃勃。龍麟、鳳翼喻孔子之道,巽風喻天。言七十子得孔子而師事之,天實助之,以成其名也。勃勃乎其不可及也,世德堂本作「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者,七十子之成名皆以孔子,
七十子之弟子源遠而流益分,不復能有所附麗以成其名,然則七十子之遭際,豈得與其弟子之遭際相提並論也!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疏〕「七十子之於仲尼也」,司馬云:「宋、吳本作『七十二子』。」按:孟子云:「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本書學行云:「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皆舉成數言之,此亦同。宋、吳本非。「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者,聖人之言行,如天道之日新,學者得聖人而師之,其進益無有已時也。「文章亦不足為矣」者,司馬云:「言游孔門者,務學道德,不事文章。」按:謂七十子不必皆有著述傳於後世,非其才有所不逮,乃日有所不給,亦意有所不屑也。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非絕德邪?」〔注〕是皆德之殊絕。「力」。〔注〕絕力者何?「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邪?」〔注〕此等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疏〕「君子絕德,小人絕力」者,絕謂不可幾及。言君子小人各有其不可幾及者,君子之於德,小人之於力是也。「舜以孝」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中庸云:「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禹以功」者,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左傳昭公篇云:「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皋陶以謨」者,皋陶謨云:「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書序云:「皋陶矢厥謨。」「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者,秦本紀云:「惠王卒,子武王立。」索隱云:「名蕩。」按:本紀稱武王者,省言之。下云「悼武王后出歸魏」,又始皇本紀云「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是以二字為謚也。本紀又云:「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八月,(按:悼武四年。)武王死,族孟說。」是烏獲、任鄙皆秦悼武王同時人。孟子云:「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趙注云:「烏獲,古之有力人也。」則烏獲乃古有力者之稱。秦悼武王時之烏獲,以有力著,因取此名名之耳。梁氏玉繩漢書人表考云:「案文子自然篇,老子曰:『用眾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是古有烏獲,後人慕之,以為號也。」樗里子甘茂列傳云:「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音義:「扛鼎,音江。」司馬云:「抃牛,謂以兩牛相擊,如抃手狀。」按:張平子思玄賦舊注云:「抃,手搏也。」又通作「卞」,漢書哀帝紀贊蘇林注云「手搏為卞」,是也。然則抃牛即手搏牛之謂。殷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紂倒曳九牛。」 注「是皆德之殊絕」。按:司馬長卿封禪文:「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是殊、絕義同。 注「此等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按:世德堂本無「此等」二字。秦本紀:「舉鼎絕臏。」集解引徐廣云:「一作『脈』。」弘範所據史記,字蓋作「脈」,故云崩中。內經陰陽別論云:「陰虛陽搏謂之崩。」王注云:「陰脈不足,陽脈盛搏,則內崩而血流下。」即其義。史記惟言秦武王舉鼎而死,今按告子孫疏引皇甫士安帝王世說(當作「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則烏獲蓋亦不得其死。任鄙死狀未聞。白起列傳云:「昭王十三年,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則鄙至昭襄王時猶存。弘範云此等皆以舉重死,或別有所本。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
若荊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注〕或人之問勇,猶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答以俎豆,子雲應之以德義。〔疏〕「若荊軻,君子盜諸」者,刺客列傳云:「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索隱云:「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荊、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又同傳正義引燕太子篇云:「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吳云:「為燕太子刺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大盜耳。」司馬云:「比諸盜賊。」按:義詳後文。「請問孟軻之勇」,治平本無「問」字,錢本同,今依世德堂本。「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者,吳云:「養浩然之氣,勇之大者。」按:「孟子云:『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趙注云:「孟子勇於德。」又:「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又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其於勇也,其庶乎」者,荀子性惡云:「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義。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亡貧窮(一),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共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 注「或人」至「德義」。按:世德堂本「猶」作「若」;「應之以德義」,無「之」字。
(一)「亡」字原本訛作「雖」,據荀子性惡篇改。
魯仲連●而不制,〔注〕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祿賞。藺相如制而不●。〔注〕好義崇理,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時之務也。〔疏〕「魯仲連●而不制」者,魯仲連鄒陽列傳云:「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魯仲連見新垣衍曰:『昔者齊湣王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不敢復言帝秦。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為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魯連書,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音義:「●與蕩同。」司馬云:「宋、吳本『●』作『●』,『制』作『剬』。介甫曰:『●古蕩字,剬古制字。』」按:說文:「愓,放也。」古書多假「蕩」為之。●、●皆「愓」之俗。玉篇:「●,他莽切,直也。」非此文之義。五帝本紀:「依鬼神以剬義。」正義云:「剬古制字。」梁氏志疑云:「古制字作『制』,若『剬』,音端,與『剸』同。則『剬』乃『制』之訛矣。」按:篆文制作「●」,隸變作「●,傳寫遂誤為「剬」耳。●謂自適,制謂自持。魯仲連●而不制,謂其能輕世肆志,而不能仕官任職。藺相如,見重黎疏。制而不●,謂其能懲忿以先國家之急,而嘗為宦者令繆賢舍人,亦降志辱身矣。司馬云:「仲連不以富貴動其心,而未能忘死生;相如不以死生動其心,而未能忘富貴,故云然。」溫公意以此為承上章而言,故釋之如此,然義似未確。 注「功成而不受祿賞」。按:世德堂本作「爵賞」。 注「好義崇理」。按:世德堂本作「崇禮」。
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慷辭免罿,幾矣哉!」〔注〕鳥罟謂之罿,猶人之縲紲。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詞,得以自免,亦已危矣。〔疏〕史記鄒陽與魯仲連同傳,既論魯仲連,故遂及鄒陽也。彼傳云:「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忌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太史公曰:「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未信而分疑」者,宋云:「言未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解以免,固亦危矣。」司馬云:「孔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陽初仕梁,未為孝王所信,而深言以觸機事,分取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分疑。」吳胡部郎玉縉云:「疑,謗也。未信而分疑,未信而致與人分謗也。鄒陽云:『為世所疑。』謂為世所謗,楊子蓋本此。」榮按:鄒陽書云:「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是書意以疑、信對舉,疑即不信之謂。曲禮:「分爭辯訟。」鄭注云:「分、辯皆別也。」然則分疑即辯疑,似以宋義為長。「慷辭免罿」者,音義:「慷辭,苦兩切。免罿,音衝。」按:說文:「抗,扞也。」引伸為不詘之義。慷辭即抗辭,史云鄒陽辭不遜,及云抗直不撓,是也。「幾矣哉」者,音義:「幾矣,音機。」按:重黎云:「如辯人,幾矣!」與此同義。 注「鳥罟謂之罿」。按:說文:「罿,罬也」;「罬,捕鳥覆車也」。爾雅釋器:「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王氏筠說文釋例云:「覆車,吾鄉謂之翻車,不用罔目,以雙繩貫柔條,張之如弓,繩之中央縛兩竹,竹之末箕張亦以繩貫之,而張之以機。機上繫蛾,鳥食蛾則機發,竹覆於弓,而●其項矣。以其弓似半輪,故得車名。」 注「獄中出慷慨之辭」。按:弘範讀慷如字,故以為慷慨之辭。慷即「忼」之俗,說文:「慷,慨也。」又「慨」篆下云:「慷慨,壯士不得志也。」然「慷辭」字明用史公鄒陽傳贊語,意非慷慨之謂,此注似失其義。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注〕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楊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者,信陵君列傳云: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遂為上客。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公子患之,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公子誠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使將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留趙,十年不歸。秦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人往請公子,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索隱云:「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又平原君虞卿列傳云:「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又孟嘗君列傳云:「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泯王即位,封田嬰於薛。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齊泯王二十五年,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客有能為狗盜者,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齊泯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泯王,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後齊泯
对“文本于经” 说的文体学考察
篇二:荀子三十八篇
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
吴承学 陈赟
[摘要] 本文对中国古代“文本于经”这一重要命题进行考察。文章以五经的文体特质、学术源流为基础,分析五经对文体分类学的影响,同时指出古人提出“文本于经”除了为文体溯源之外,还夹杂着“宗经”或“尊体”的理论目的。荀子三十八篇。
[关键词]五经 文体 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史研究不应把古人的“常识”拒之门外。事实上,“常识”虽然不像专家专著那样以理论本身的创新性、深刻性取胜,但常识在影响上所具有的普泛性与持久性却往往是其它理论所不及的,这正是常识的研究价值所在。“文本于经”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之一①,这个命题在古代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遂成为老生常谈的套语②。近代以来,经学在激烈文化的批判中越来越边缘化,“文本于经”又成了不值一提的陋儒之见。总之,自古至今,“文本于经”说虽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命题,但尚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文本于经”说的含义相当复杂,但主要有二:一是文应本于经,这是出于对文以载道的期待,限于篇幅,本文不拟涉及;一是经为文之本,即文体原于五经。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具有丰富文学与文化内涵的问题:它既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描述,也是对文体谱系的理论建构,有时还表现出一种理论的策略。对“文本于经”的文体学研究,正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 从经学到文体学
将文章之源追溯到五经首先应该与古代学术源流说相关。汉代文学批评兴起依经立论之风气,《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作者简介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赟,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275)。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理念”与广东省重点科研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体系”的部分成果。本文写作参考了吴承学、何诗海《中国古代文体史料学》一书未刊稿。 ① 《四库全书总目》谓:“文本于经之论千古不易”(黄佐《六艺流别》提要)。古人或谓“原于经”,或谓“源于经”,或谓“本于经”,字面略有差异,意义基本相同。据古文经学的观念,经本是六经,《乐经》毁于秦火。今文经学则认为乐本无文字,只是与《诗》、礼相配合的乐曲。汉武帝只立五经博士,故又称五经,后世纳入附经之传,遂有七经、九经、十三经之说。文论上又有文本五经、文本六经之说,内涵大致相同,本文为了行文方便,采用较为常见的五经之说。
②叶燮曾感慨道:“为文必本于六经,人人能言之矣。人能言之,而实未能知之”(《与友人论文书》,《已畦集》卷十三)。
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已把汉赋与《诗经》联系起来。班固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文选·两都赋序》),确立了汉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其后王逸《楚辞章句序》“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把《楚辞》的源头归之五经。文章源于五经实际上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以五经为源头,以后世之文为流别支派。这一比喻亦来源于学术分类,《汉书·艺文志》以源流譬喻学术,“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章学诚《校讐通义·原道》),又以五经统百家之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在汉人的观念中,能归入“文章”或“文辞”的,不仅诗赋二端,还包括奏疏章表等大量实用文体。《汉书·艺文志》没有把这些文体独立出来,而是附于六艺、诸子中。如《六艺略》中《尚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奏事》二十篇,《论语》类列《议奏》十八篇。另外,史部著作也没有独立,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类。对此,刘师培《论文杂记》分析说:“观班《志》之叙艺文也,仅序诗赋为五种,而未及杂文;诚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今人之所谓文者,皆探源于六经、诸子者也。”①这个结论是有见地的。《汉志》的这种归类,一定程度启发了后世文体源于经书说。
将文章之源追溯到五经同时也与文章特质进一步受到重视,文学逐渐走向相对独立、自觉的时代发展相关。为何五经能应用到文章学之上,五经与文体究竟有何联系?五经之所以成为文章的渊源,一方面是五经本身具有文章的特质,这是潜在的前提,另一方面,汉末魏晋以降逐渐重视文章特质的时代风气也为当时人提供了在五经之中发现文章之美的意识和眼光。如果说,汉初把《诗》推崇为经,这时的文学批评则反之视经为文。傅玄说:“《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七十九)陆机《文赋》提出文章写作要“漱六艺之芳润”。任昉也说:“六经素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文章缘起》卷首)这些看法,还只是总的判断,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则将《诗经》句法与后世诗歌句法一一对接。到了六朝的刘勰与颜延之更具体地提出各体文章源出五经。至此,顺流而下的古代学术的源流,与文学逐渐自觉之后逆流而上的文体溯源交汇在一起,五经为文体之源的说法遂成为普遍的观念。
五经既是经,又是圣人之文。宋孙复《答张洞书》云:“是故《诗》、《书》、《礼》、《乐》、《大易》、《春秋》,皆文也。总而谓之经者,以其终于孔子之手,①《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尊而异之尔,斯圣人之文也。” (《孙明复小集》)因此,古人认为六经乃是文章之极致。宋陈耆卿《上楼内翰书》云:“论文之至,六经为至。”(《篔窗集》卷五)宋濂云:“文至于六经,至矣尽矣!其始无愧于文矣乎?”(《徐教授文集序》,《文宪集》卷七)。明焦竑《刻两苏经解序》:“文之致极于经。”(《澹园续集》卷一)五经既然是文之极致,那么,五经的体类自然也就成为文章文体分类的渊源。近人王棻云:“文章之道,莫备于六经。六经者,文章之源也。文章之体三:散文也,骈文也,有韵文也。散文本于《书》、《春秋》,骈文本于《周礼》、《国语》,有韵文本于《诗》,而《易》兼之。文章之用三:明道也,经世也,纪事也。明道之文本于《易》,经世之文本于三《礼》,纪事之文本于《春秋》,而《诗》、《书》兼之。故《易》、《书》、《诗》者,又六经之源也。”(《柔桔文抄》卷三)叶燮《与友人论文书》说:“六经者,理、事、情之权舆也。合而言之,则凡经之一句一义,皆各备此三者,而互相发明;分而言之,则《易》似专言乎理,《书》、《春秋》、《礼》似专言乎事,《诗》似专言乎情。此经之原本也。而推其流之所至,因《易》之流而为言,则议论、辨说等作是也;因《书》、《春秋》、《礼》之流而为言,则史传、纪述、典制等作是也;因《诗》之流而为言,则辞赋、诗歌等作是也。数者条理各不同,分见于经,虽各有专属,其适乎道则一也。而理与道为体,事与情总贯乎其中,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已畦集》卷十三)总之,在古人看来,文章的类别与文体,都可以追溯到五经。
二 从经各有体到文体分类
把各类文体分别归于某经,其理论前提是经各有体。前人对此论述很多,考察六经差异主要有两种角度,一是各经的整体风格不同。《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荀子·劝学》:“《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徳,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偏举其详也。”《汉书·艺文志》:“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既然六经有不同体制,那么文本于经,便可以从中吸收不同类别的营养。《文心雕龙·宗经》所论甚多,此不赘论。韩愈《进学解》荀子三十八篇。
谈到吸收各种不同的学术养分时说:“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柳宗元谈自己的写作经验时就更具体地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源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枝,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河东集》卷三十四)柳宗元所本,以经为主,从不同经典获得不同的文风。
二是五经在内容与文体上互有差异。诸经各有分工,各擅其事,共同组成一个彼此各有特色,整体又比较完备的体系,包括了古代各方面的知识,所以古人认为许多学术类别都源于五经。章学诚《立言有本》:“史学本于《春秋》,专家著述本于《官礼》,辞章泛应本于《风诗》,天下之文,尽于是矣。”(《章氏遗书》卷七)。五经本身确已有一定的文体意识。就一书之中而言,《诗经》就有风、雅、颂之别,《尚书》中的诰、誓、命、训也各有差别。就整书而言,五经各有不同特色。五经是否各自有体?表面上看,似乎有不少人否定这种观念。宋陈骙在《文则·上》中认为: “六经之道既曰同归,六经之文容无异体。故《易》文似《诗》,《诗》文似《书》,《书》文似《礼》。”明苏伯衡《空同子瞽说》:“《易》有似《诗》者,《诗》有似《书》者,《书》有似《礼》者,何体之有?”(《苏平仲文集》卷十六)我们要注意到,这些说法正是针对当时的常识而言的,所言乃是普遍中的个别情况。他们的说法,潜藏的更深层的观念背景正是经各有体。对此古人所论甚多。《庄子·天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经体之别,对于文体分类学有深远的影响。这里举两个比较少为人所注意的例子。元郝经《郝氏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上上 “文章总叙”将历代文章归入《易》、《书》、《诗》、《春秋》四部,其中《易》部有序、论、说、评、辨、解、问、难、语、言诸体;《书》部有国书、诏、册、制、制策、赦、令、教、下记、檄、疏、表、封事、奏、议、笺、启、状、奏记、弹章、露布、连珠诸体;《诗》部有骚、赋、古诗、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诸体;
《春秋》部有国史、碑、墓碑、诔、铭、符命、颂、箴、赞、记、杂文诸体。郝经把各体文章分别归入四部经书中,每部之下的总序,分论各体的小序,集中体现了郝经的文体学思想。如《易》部总序:“昊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为天地人物无穷之用,后世辞章皆其波流余裔也。夫繇、彖、象、言、辞、说、序、杂,皆《易经》之固有,序、论、说、评、辨、解、问、对、难、语、言,以意言明义理,申之以辞章者,皆其余也。”《书》部总序:“《书》者,言之经。后世王言之制,臣子之辞,皆本于《书》。凡制、诏、赦、令、册、檄、教、记、诰、誓,命戒之余也,书、疏、笺、表、奏、议、启、状、谟、训,规谏之余也。国书、策问、弹章、露布,后世増益之耳,皆代典国程,是服是行,是信是使,非空言比,尤官样体制之文也。”《诗》部总序:“《诗经》三百篇,《雅》亡于幽、厉,《风》亡于桓、庄。历战国先秦,只有诗之名而非先王之诗矣。本然之声音,郁湮喷薄,变而为杂体,为骚赋,为古诗,为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其体制不可胜穷矣。”《春秋》部总序:“《春秋》、《诗》、《书》,皆王者之迹,唐虞三代之史也。孔子修经,乃别辞命为《书》,乐歌为《诗》,政事为《春秋》,以为大典大法,然后为经而非史矣。凡后世述事功,纪政绩,载竹帛,刊金石,皆《春秋》之余,无笔削之法,只为篇题记注之文,则自为史而非经矣。”这些总序,解释文体归类的原因或依据,反映了以经为本,追溯文体源流的文学思想。
明代黄佐的《六艺流别》一书是体现“文本于经”文体学理念的集大成者,此书首次用文章总集的形式把古代各体文章分别系之《诗》、《书》、《礼》、《乐》、《春秋》、《易》之下,形成六大文体系列,重新建构了一个庞大的中国古代文体谱系。黄佐在《六艺流别序》中引用董仲舒的话:“《诗》道志,故长于质。《书》著功,故长于事。《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春秋》司是非,故长于治。《易》本天地,故长于数。”很明显,黄佐的文体分类,是建立在经体分类理论之上的。他在《序》中认为六经的功能分别是:《诗》“道性情”,“《诗》艺”主要包括诗赋文体;《书》“道政事”,“《书》艺”主要包括公文文体;《礼》主“敬”,“《礼》艺”主要包括礼仪文体;《乐》主“和”,“《乐》艺”主要包括音乐性文体;《春秋》主“名分”,“《春秋》艺”主要包括叙事与论说文体;《易》主“阴阳”,“《易》艺”主要包括术数类文体(《明文海》卷二百十九)。该书建构了一个以经为本的文体谱系:
《诗》艺:谣、歌。谣之流其别有四:讴、诵、谚、语。歌之流其别
有四:咏、吟、叹、怨。诗之流不杂于文者其别有五: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附:离合、建除、六府、五杂组、数名、郡县名、八音。)诗之杂于文者其别有五:骚、赋、(附:律赋)词、颂、赞。(附:诗赞)
天行人自强
篇三:荀子三十八篇
天行健 人自强
——中国武术荀子三十八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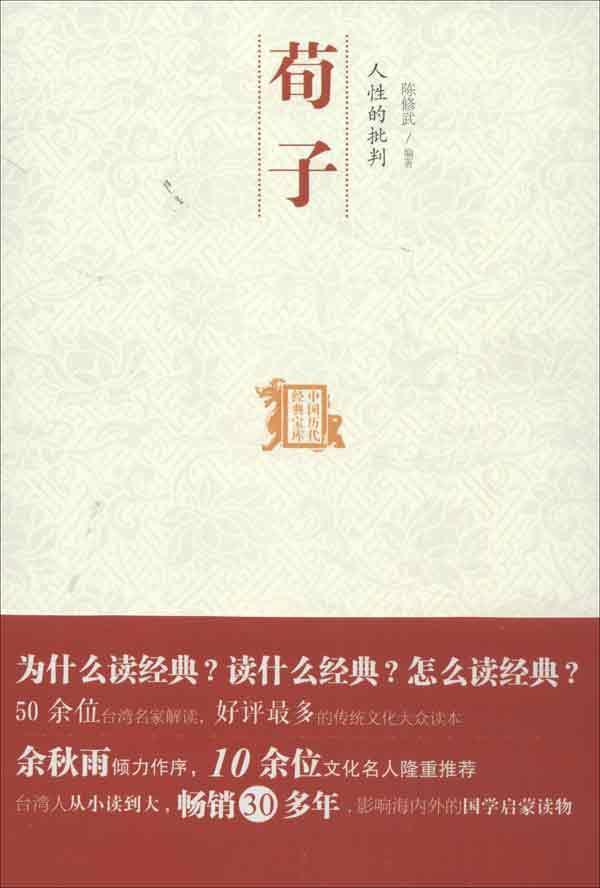
主编:
执行主编:朱立元
委员:
总策划:
责任编辑:封兆才
封面设计:曾一中
张岱年 王振复 石铜钧 李祥年祝乃杰庆芳 周振鹤 葛剑雄葛君 田雪峰 盛渊 朱立元 涌豪
一、 法自然之理,成人文之象 ——中国武术的渊源
中国武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熔实战、养生、表演为一炉的运动项目,它注重内外兼修,形神俱备,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早在五、六十万年前的原始旧石器时代,人类为了生存,首
先要与自然界的各种猛兽作斗争,人类就已经制造和使用了砍砸器,如石锤、燧石、尖嘴凿等粗制石器,以及用石器刮削过的棍棒。这些极原始的工具,既是打猎和捕鱼等生产用的工具,又是与猛兽斗争中自卫生存的武器。他们在使用这些粗糙的石器、木器与野兽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地获得了徒手搏斗和捕杀的技能。这些简单的技击动作,虽然大多出自动物求取生存的本能,但它却是中国武术的萌芽。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磨制的石斧、石铲、石刀、鱼骨叉
和石头矛等石器被人们普遍地使用,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末期,铜的开采和铜器的使用,使原始的生产工具有了很大的进步,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它也为后来武术动作中劈、刺、砍、扎等技术的逐步形成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石斧、石刀的发明使用,才使人们获得了“劈、砍”的概念;尖状石器的发明使用,才使人们有了“刺”的概念;鱼骨叉等的发明使用,才使人们有了“扎”的概念。这些原始的生产工具或自卫生存的武器,也就是后来武术器械的前身。如:鞭、锏是由短棒演变而来的;绳镖是由鱼骨叉等演变而来的。此外,从原始的“投球绳套”与现在的流星锤;原始的石刀、石斧与现的铁刀、铁斧中,都不难看出它们演变和发展的痕迹。
随着人们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人们的生
存条件介到了一些改善,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有了些剩余。于是,氏族、部落之间的原始战争便随之出现了。原始战争的出现,促进了武术的形成,使武术在已有的狩猎格斗和捕杀技能的基础上,又有了军事战斗技能的发展。在战争的实践中,自然地形成了许多徒手或手执木石器械等的拼杀格斗动作。同时,人们为了个人及民族部落的生存,便把从战争实践中获得的一切格斗技能加以总结,逐渐地把它们规范化、程式化,并如同狩猎等生产技能一样传授给年轻一代。于是最原始的,以技击为主的武术便形成了。从史籍中可以看到,周朝已有了“拳勇”、“技击”、“相扑”等武术词汇。周武王曾留下《剑铭》、《弓铭》、《书剑》、《书刀》诸篇
以教子民。因此,以技击格斗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武术最晚应形成于商周时期。
远古的人类为了生存,除了与自然界的猛兽作斗争,还要与凶猛的洪水,恶劣气候作斗争。生存环境的险恶使疾病滋生,而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人们在生产和习武的实践中逐渐地认识到武术除了军事战斗作用外,还具有强身健体、养生治病的作用。《吕氏春秋》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昔日康氏之始,民气郁阏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舞以导之。”这里所说的“作舞”,当然包括拼杀格斗动作的模仿演练。古人将“筋骨瑟缩不达”的原因释为“气郁瘀滞著”,并且采用作舞宣导的方法来解决。《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篇》也有这样的记载:“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按这些“按蹻、导引”实际上就是气功的别称,“气”的概念及其导引方法的出现便为中国武术中以养生为主的内家拳这一流派的产生,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远古人类在与自然界中凶猛野兽作斗争的过程中,学会了一些技击格斗之术;在与天、地、生存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养生治病的方法。这便是中国武术的两大渊源。纵观中国武术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可知,中国武术的主要功用不外乎两种:一是军事战斗方面的作用,主要以技击格斗为表现形式;二是养生医学方面的作用,主要以气功导引为其表现形式。两种不同的功用,使中国武术史上出现了影响深远的两大流派,即:外家拳和内家拳。
内家拳、外家拳,这两大流派的发展是极不平